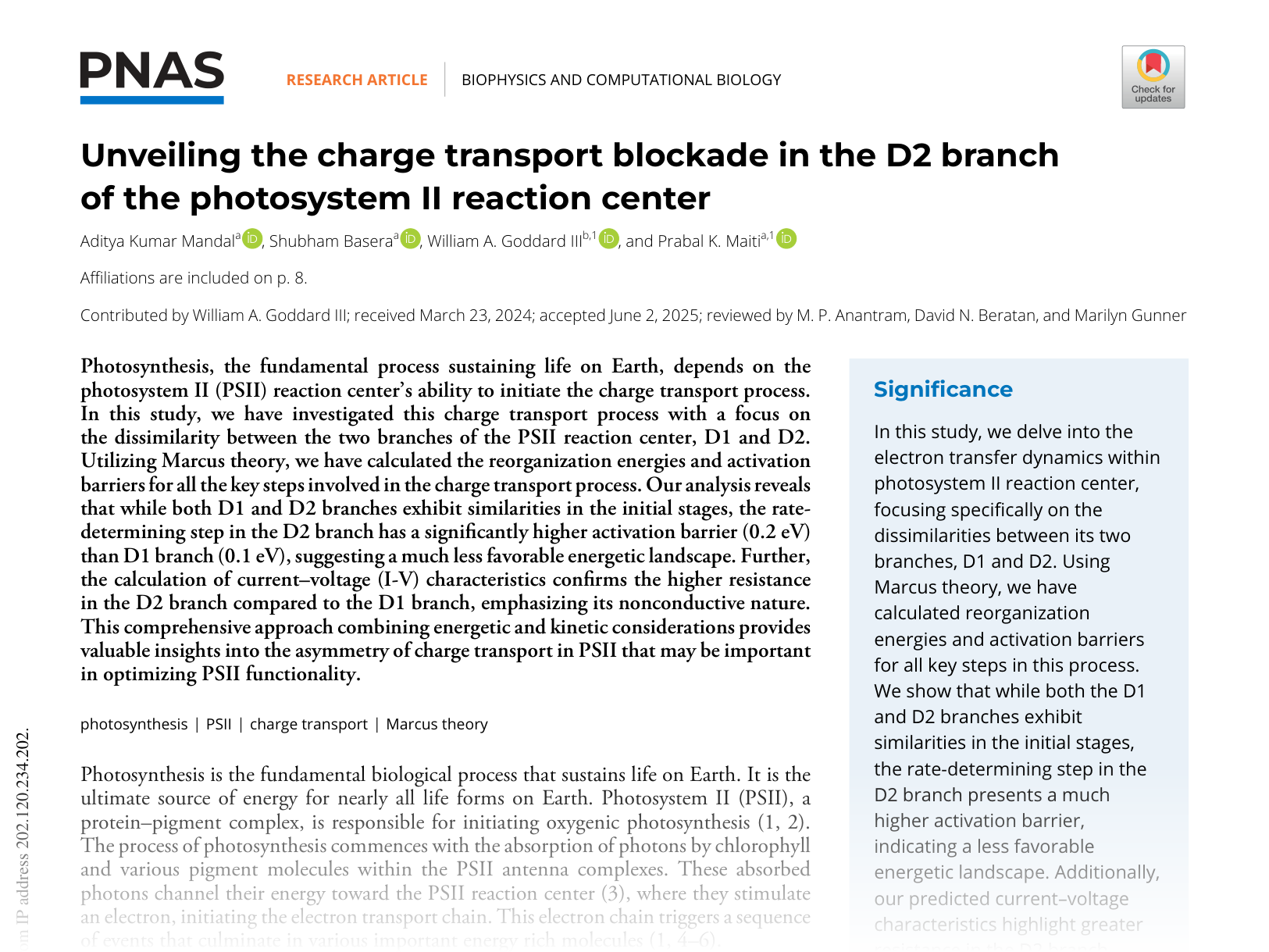光合作用是地球上最重要的生物过程。它就像我们星球的天然太阳能电池板,将阳光转化为化学能,为几乎所有生物体提供能量。这一过程的核心是一种被称为 光系统 II (PSII) 的分子机器——它负责分解水并释放氧气。
PSII 的结构既对称优美,又充满谜团。其核心部分称为 反应中心 (RC) ,拥有近乎完美的 C2 对称性,包含两条潜在的电荷传输通路,通常称为 D1 和 D2 分支。在结构上,这两条分支互为镜像。然而,只有其中之一——D1 分支——在传递电子时是活跃的,而 D2 分支尽管是它的分子孪生体,却显得惰性十足,仿佛一根“断了的导线”。
几十年来,科学家们不断追问: 为何自然要构建一个如此完美对称的机器,却让其中一半处于闲置状态? D2 分支究竟是备用方案、进化的遗迹,还是被刻意关闭的元件?
近期发表在《美国国家科学院院刊》 (PNAS) 上的一项研究为这一谜题提供了迄今为止最清晰的答案。研究人员结合了 分子动力学 (MD) 模拟与电子转移化学的核心理论——马库斯理论 (Marcus Theory) ,绘制出两个分支的能量学与动力学图景。计算表明,D2 分支存在明显的 能量阻断,有效阻碍了电荷传输。这一发现为 D2 分支的失活提供了决定性的能量学解释。
光合作用的能量引擎
在深入能量计算之前,让我们先了解一下这台分子机器。光系统 II 是一个巨大而复杂的蛋白质–色素复合物,嵌入在叶绿体膜中。它通过捕获光子,引发一系列电子转移反应,从而启动放氧光合作用。

图 1. PSII 复合物及其天线蛋白 CP43 和 CP47 (图 A) ;反应中心的放大视图显示沿 D1 和 D2 分支排列的色素辅因子 (图 B) ;以及沿活性 D1 分支的电荷传输路径 (图 C) 。
PSII 内部的 反应中心 (RC) 由若干关键色素分子组成,它们沿着两条对称分支排列:
- 叶绿素: \(P_{D1}\)、\(P_{D2}\)、\(Chl_{D1}\)、\(Chl_{D2}\)
- 脱镁叶绿素: \(Pheo_{D1}\)、\(Pheo_{D2}\)
- 末端受体: \(Q_A\) (D1 分支) 、\(Q_B\) (D2 分支)
当光被天线复合物吸收后,能量汇聚到反应中心,在那里驱动电子沿 D1 分支依次传输:
- 初始电荷分离:
一个电子从中心叶绿素 \(Chl_{D1}\) 跃迁至脱镁叶绿素 \(Pheo_{D1}\),形成状态 \(Chl_{D1}^+Pheo_{D1}^-\)。 - 空穴转移:
正电荷 (“空穴”) 从 \(Chl_{D1}\) 移向 \(P_{D1}\)。 - 电子转移:
电子从 \(Pheo_{D1}\) 传递到醌分子 \(Q_A\),完成反应链。
这一系列过程在万亿分之一秒内完成,启动了驱动光合作用的复杂级联反应。那么如果 D2 分支在结构上完全相同,为什么它却无法完成相同的步骤?
为了探明这一点,研究人员需要一种方式来量化两个分支中每个电子转移步骤的“难易程度”。
用马库斯理论描绘能量地貌
为了评估电子转移效率,研究团队采用了 马库斯理论 (Marcus Theory) ——这一荣获诺贝尔奖的理论框架描述了电子在波动环境中如何在供体与受体分子之间迁移。

图 2. (A) 电子从供体 (D) 转移到受体 (A) ,引发溶剂构象改变。(B) 反应物与产物状态的自由能抛物线,其中活化能垒 \(\Delta G^{\dagger}\) 标示了反应过渡点。
马库斯理论将原子运动的复杂性简化为一个 反应坐标,以两条抛物线表示系统能量——一条对应反应物 (电子仍在供体上) ,另一条对应产物 (电子已转移) 。
该过程由三大参数决定:
- 驱动力 (\(\Delta G_0\)) ——反应物与产物之间的自由能差。
- 重组能 (\(\lambda\)) ——电荷转移后重新调整分子及溶剂环境所需的能量。
- 活化能垒 (\(\Delta G^{\dagger}\)) ——区分两个状态的能量峰;能垒越小,电子转移越快。
这些量遵循下式关系:
\[ \Delta G^{\dagger} = \frac{(\lambda + \Delta G_0)^2}{4\lambda} \]而转移速率表示为:
\[ k_{CT} = \frac{2\pi}{\hbar}\frac{|J_{DA}|^2}{\sqrt{4\pi\lambda k_BT}}\exp\left(-\frac{\Delta G^{\dagger}}{k_BT}\right) \]其中 \(J_{DA}\) 表示供体与受体之间的电子耦合。
研究人员借助 分子动力学模拟,追踪了 PSII 反应中心中数千个原子的动态变化。对于每一个电子转移步骤,他们在每个时间快照中计算出 垂直能量差: \(\Delta E = E_\text{product} - E_\text{reactant}\)。
将这些能量差的 概率分布 \(P(\Delta E)\) 绘制出来后,得到两条高斯分布曲线——分别代表反应物与产物。它们中心的间距等于重组能的两倍 (\(2\lambda\)) 。

图 3A. 能量差分布的高斯曲线间距决定了重组能 \(\lambda\)。
这些分布可通过以下公式直接转换为 自由能抛物线:
\[ \Delta G = -k_BT \ln[P(\Delta E)] \]
图 3B. 将 \(P(\Delta E)\) 曲线转换为自由能曲线,可直接得到活化能垒 \(\Delta G^{\dagger}\)。
这一框架使研究人员能够精确确定两个分支中各个电荷转移步骤的活化能垒。
结果: 锁定阻断的源头
活跃的 D1 分支——顺畅无阻
首先,团队分析了电子流动已充分证实的 D1 分支。

图 4. D1 分支三步电荷转移的能量差分布与自由能曲线: 步骤 1 (\(Chl_{D1} \rightarrow Pheo_{D1}\)) 、步骤 2 (\(Chl_{D1}^+ \rightarrow P_{D1}^+\)) 、步骤 3 (\(Pheo_{D1}^- \rightarrow Q_A^-\)) 。
计算结果如下:
| 步骤 | 过程 | 活化能垒 (\( \Delta G^{\dagger} \)) |
|---|---|---|
| 1 | \(Chl_{D1} \rightarrow Pheo_{D1}\) | 0.073 eV |
| 2 | 空穴转移 \(Chl_{D1}^+ \rightarrow P_{D1}^+\) | 0.058 eV |
| 3 | \(Pheo_{D1}^- \rightarrow Q_A^-\) | 0.13 eV |
这些低能垒说明该分支具有优异的电子导通性能——能量图景平滑,就像缓缓下落的坡道,电子轻松即可滑行通过。
沉默的 D2 分支——迎面撞墙
将相同分析应用于 D2 分支,问题随之显现。

图 5. D2 分支的能量差分布。前两步与 D1 分支相似,而第三步出现了显著的能垒。
| 步骤 | 过程 | 活化能垒 (\( \Delta G^{\dagger} \)) |
|---|---|---|
| 1 | \(Chl_{D2} \rightarrow Pheo_{D2}\) | 0.063 eV |
| 2 | 空穴转移 \(Chl_{D2}^+ \rightarrow P_{D2}^+\) | 0.061 eV |
| 3 | \(Pheo_{D2}^- \rightarrow Q_B^-\) | 0.24 eV |
前两步并无障碍,但第三步——电子最终传递至醌 \(Q_B\) 时——遭遇了高达两倍的能量壁垒。
为了进一步验证,研究人员进行了 量子力学 (QM) 计算,考虑了蛋白质与辅因子之间的精细相互作用。

图 6. 量子力学计算得到的速率决定步骤活化能垒。D2 分支的能垒约比 D1 高 0.4 eV。
QM 结果显示,D2 分支的能垒比 D1 高约 0.4 eV。而室温下的热能仅约 0.025 eV,因此该能垒几乎完全阻断电子通过——就像一堵高不可攀的墙壁。
能量壁垒化作电阻
电子无法轻易在辅因子之间跃迁,就会表现出极差的导电性。为了直观展示这一点,研究团队模拟了两个分支的 电流–电压 (I–V) 特性,在分子电路两端施加虚拟电压。

图 7. (A–B) 对 D1 与 D2 分支分子电路施加电压的示意图。(C) 电流–电压特性显示 D2 分支 (红色) 电流显著低于 D1 分支 (蓝色) 。
在相同电压下,D2 分支的电流远低于 D1 分支。推算出的电阻表明,D2 的电阻约高出两个数量级——这是能量壁垒在电学上的直接体现。
能量学与动力学数据的完美对应勾勒出清晰的全貌: D2 分支无法导电,源自其不利的能量地貌。
自然的巧思: 断线的意义
这项研究解开了困扰科学界数十年的 PSII 结构之谜。尽管外观上对称,D1 与 D2 两个分支却在功能上天差地别:
- 瓶颈仅出现在步骤 3——醌转移阶段;
- D2 的活化能垒约高出 0.4 eV,使得电子转移在热力学上几乎不可行;
- 这导致巨大的电阻,使 D2 分支几乎不具导电能力。
这些差异可能源于局部蛋白质环境的微妙变化——辅因子周围的氨基酸组成、静电场和溶剂化模式的不同。自然通过这些精细调控的能量不对称性,确保电荷流动具有明确方向,使电子仅沿一条高效路径传输。
换句话说,D2 分支的失活并非缺陷,而是自然的精妙设计。通过有意“断开”一根导线,自然保障了 PSII 复杂光化学反应的单向能量流与稳定性。
理解这一机制不仅深化了我们对光合作用内在机理的认识,也为开发 人工光合作用系统 与 仿生太阳能装置 提供了新思路。这提醒我们: 结构的对称不必意味着功能的对称,正如自然最优雅的设计中,常常蕴含着刻意的不平衡。